肥胖政治及其與酷兒性的交織
在異性戀環境中以肥胖和不被慾望的狀態長大,代表我覺得被去女性化並被性別排除在外,因為我「塞不下」。
身體非二元翻譯著作
強納森
6/15/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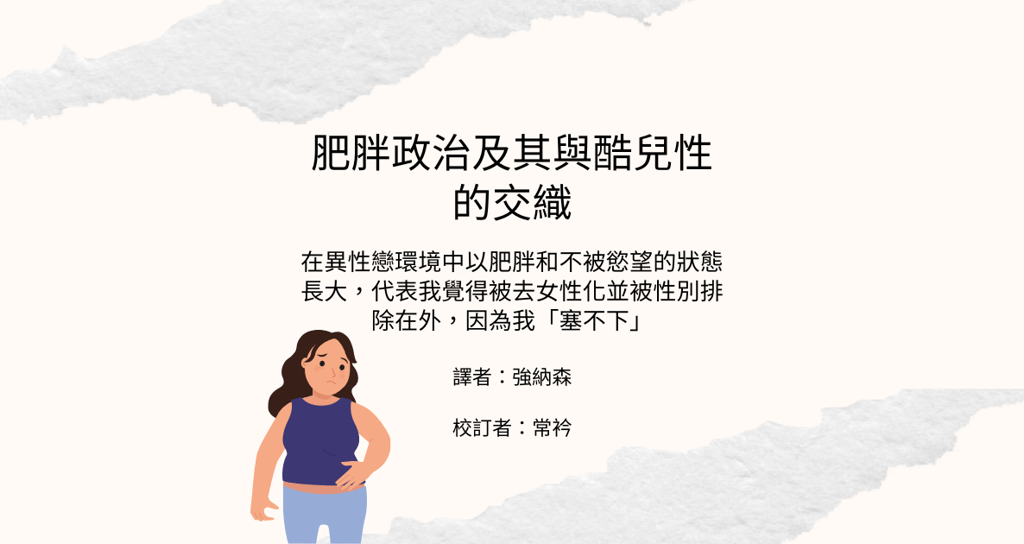

【翻譯著作】肥胖政治及其與酷兒性的交織
本篇文章原刊於 Feminism in India
原文作者:Nandini Desiraju
原文出版日期:2021/09/07
譯者:強納森
校訂者:常衿
譯者筆記:
身為一個與肥胖掙扎數十載的人,小編真的可以深深體會這一篇的內容,以及為何我身體的樣貌與我的酷兒性有關。分享給我們的肥胖酷兒朋友,希望可以帶來一股甘泉~
#肥胖 #酷兒 #交織性 #非二元
情緒觸發警示:本篇文章提及恐胖、飲食疾患、自殘、性侵
我是個21歲的非二元胖子,出生指定性別為女。在我有記憶以來,我的身體就受到令人痛苦的大量嘲諷、厭惡及控制。我還小的時候,我的飲食被控制到我直到今天都還無法理解我身體的飢餓訊號的程度。我當時所吃下去的食物都是秘密、羞愧的暴食 —— 一個後來滾雪球般變成一輩子失序飲食的習慣。
讀書時,像我這樣的身體基本上是被去人性化的。我被標籤為水牛、BST公車、或坦克車(軍校的惡霸可以很脈絡恰當)。在義務健檢時,我的體重被大聲宣讀,供我所有一般身材的同學嘲諷;接下來幾個月期間,這組數字成為我僅存的身分。我記得我當時希望得癌症或其他疾病好讓我減重,並掙脫這個枷鎖。
節食文化要求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即使需要賠上心理和身體健康)的減去「多餘」的體重,變得「更健康」。伴隨著節食文化的是肥胖羞辱的文化,但這種文化其實適得其反,因為它使肥胖者不願接觸健康減重的相關資源。除此之外,節食文化及健康指標,以及健康主義本身,都是根基於種族主義及健全主義。營養師 Kéra Nyemb-Diop 認為,像生酮飲食這樣的飲食習慣是一種洗白,且將原住民食物邊緣化為不健康的。同時,像是牛尾這樣的食物被仕紳化,並以「奢華的高級食品」的名義來販賣。甚至連身體質量指標(BMI)這個用來衡量良好健康的國際指標,也是完全根據白人、歐洲受試者發展出來的。Audrey Gordon 表示,BMI被用來當作推動優生學的科學理據,也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開始根據身高體重決定保費比率後,變成評估健康的標準。
節食工業複合體靠著反肥胖及個人不安全感來大賺一筆。Da’Shaun Harrison 寫道,「教導人們憎恨自己的身體有賺頭;如何看重瘦的身體;如何將美食與罪惡感連結」。肥胖的慾望 — — 吃、色、存在 — — 被汙名化為道德的墮落,健康的責任因而從國家及資本轉移到個人身上。資本主義一邊生產及推動不健康的生活模式,一邊販賣健康的「權宜之計」;它透過兩者營利,卻不為任何一方負責;國家對於提供安全及可負擔的醫療服務無所作為。正因如此,肥胖解放必須徹底廢除節食工業複合體。我還記得成長過程中,感到自己的一舉一動 — — 吃、跑、運動、甚至是學習 — — 時時被那些一心只想嘲諷我的苗條同學監視,以他們肉慾的目光。關於肥胖的展演,Stefanie A. Jones 寫道:
「由於情境的作用,(肥胖的)身體必然表現得像一個肥胖的身體。雖然日常生活中,肥胖的展演者仍有許多表現自我的空間;但觀眾的目光如此沉重,大幅影響了演出的意涵,以至於展演者的工作(work)必然是在重現觀眾的期待」。
雖然我一直感覺到這種展演的重量,我未曾理解到的是這種展演也是具有酷兒性的。
Jackie Wykes 強調肥胖與酷兒性的相似性。兩者都被醫療化及病理化 —— 那些號稱能「治好」這些「疾病」的「療法」,如根除酷兒性的電療法,或最近的 齒瘦法 減重裝置(將下巴鎖住,並限制使用者只能吃流質食物),都是既傷身又無事實根據的。酷兒性和肥胖都被抹黑為不自然和不節制的;兩者都被認為是該被拔除的道德危機。結果是,肥胖和酷兒的身體被邊緣化,並被標籤為生理及道德上的「不合格」。
在主要透過慾望被理解的性別二元框架中,肥胖的身體被去性化,且被視為不值得被愛。我從未被認為是「具吸引力的」;聽說我進入一段浪漫或性關係,別人往往非常驚訝我竟然「有辦法」找到對象。甚至是我受到性侵的經驗都被同儕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我曾經強迫我自己繼續忍耐恐怖情人,或在不舒服的時候還同意某些行為 —— 因為我相信我永遠無法有「更好的選擇」。
在異性戀環境中以肥胖和不被慾望的狀態長大,代表我覺得被去女性化並被性別排除在外,因為我「塞不下」。
我能取得且覺得舒服的服飾也形塑了我的性別認同。大部分的服飾店只提供少量的大尺碼女裝。在我的經驗中,即使有大尺碼的衣服,設計上還是針對一般尺寸的身體。XL/XXL 的汗衫和連帽衣很常見,但是褲子就不是這麼回事了。原因是:XL 的汗衫並不是給肥胖的個體穿的,而是給想要穿過大尺碼的一般體型的人穿的。
與家人一起逛街一直都是近乎折磨的經驗。我在充滿羞恥的更衣間的禁錮中,塞進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全都是盡可能最小的尺碼,而我尋找任何穿得下的衣物的努力卻一直未果。我從不曾被允許購買露出皮膚的衣服 —— 這包括短褲和無袖上衣 —— 因為我這樣會看起來「很不體面」。他們告訴我「買對你來說有點小的衣服,這樣會鼓勵你減重」但這從來沒有發生,而我最後總是有一堆不合身的衣服。我穿著女裝的時候感覺像一個冒牌貨,因此我在對我而言更合身的男裝中找到慰藉。我現在和過去唯一知道如何表現我性別的方式,是肥胖。
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有飲食障礙的問題。有時候我一天吃不到100–200卡路里;有時候,我吞下任何我找得到的食物,只為了接下來花好幾小時,蹲在馬桶邊努力吐出所有嚥下去的東西。在這些時候,我痛恨我身體的一切,痛恨它表現出來的樣子,然後轉向自殘。我必須承認,這些經驗的確某些程度加劇了我的性別不安。我這麼說,並不是想要將性別不安病理化,而是為了表示,我的肥胖一方面讓我覺得自己「辜負」了性別,也同時強迫我服膺於這個性別框架。
肥胖可能對其他肥胖、性別不羈及跨性別的個體來說只有些許或毫無影響;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削減他們的經驗。但,對我來說,肥胖一直都是我的性別。認同自己是非二元者,讓我更有能力面對那些一直以來無力掌控的社會結構,也讓我更能夠處理對自己的身體所感到的羞恥。我很感謝我來自 LGBTQ+ 社群的朋友和盟友;與他們的政治性談話允許我超越我恐同並恐胖的成長過程,並在酷兒身分中找到基進的慰藉。
. . .
參考資料
1, 2. 肥胖體現的酷兒化, ed. Cat Pausé, Jackie Wykes, 及 Samantha Murray.
Nandini Desiraju 是一位酷兒作者,正在攻讀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你可以在IG上找到他 @dahichawal。
特別感謝《肥胖與酷兒:酷兒和跨性別者的身體和生活選集》(ed: Bruce Owens Grimm, Miguel M. Morales 及 Tiff Joshua TJ Ferentini) 的多位作者,正是他們書寫的生命故事,鼓勵筆者寫下自己的生命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