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著作】復興女同志理論:強制異性戀、異性戀常規與異性戀霸權
女同志女性主義原創著作
希維亞
4/26/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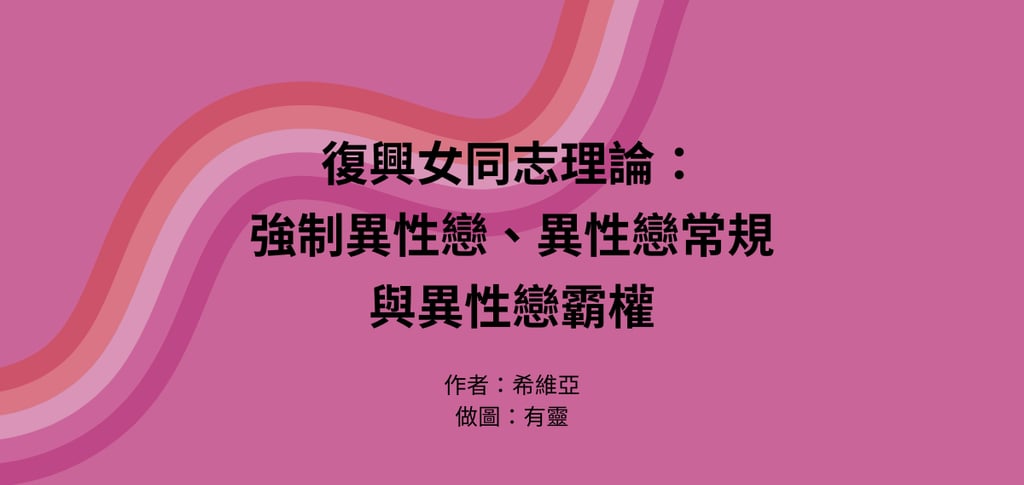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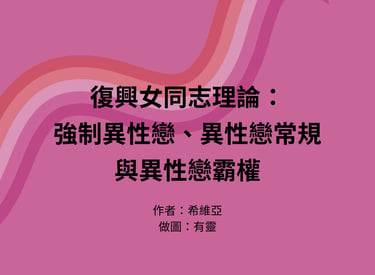
【原創著作】復興女同志理論:強制異性戀、異性戀常規與異性戀霸權
作者:希維雅
做圖:有靈
主編筆記:
酷兒翻越在今年的 #女同志現身日 ,邀請大家一起探討 #女同志理論 的獨特性,一起反思「強制異性戀」、「異性戀常規」及「異性戀霸權」之差異何在~
「強制異性戀」概念的起源
「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女性主義詩人亞卓安·芮曲(Adrienne Rich)於1980年提出,在其經典文獻〈強制異性戀與女同性戀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中,她批判異性戀並非「自然」或固有的,而是制度強加(institutionally imposed)於許多社會和文化——以確保女人處於從屬地位的結果。
芮曲延伸了基進女性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對職場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的分析,她將「女人的經濟依賴」、「對女人的性化」和「對女同志的邊緣化」等問題連結在一起,進而形成一套對女人和女同志壓迫的獨到分析:當女人被期待透過和男人的關係來獲得經濟與社會支持,不僅使女人成為「依賴人口」,也使女同志遭受社會排除和邊緣化。
另外,芮曲提出了「女同志連續體」(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強調女性之間的情感與實踐聯繫不僅限於性或浪漫關係,而是涵蓋一切形式的女性間親密、支持與團結,且一直存在於女性的文化與日常生活,只是被父權社會忽視或壓抑。芮曲企圖恢復女性之間親密關係的正當性與歷史,作為對異性戀父權的一種抵抗形式。有趣的是,芮曲意外地支持了無性戀者和無浪漫者,這甚至是早期酷兒理論未能達成的目標。
與「異性戀常規」或「異性戀霸權」的不同
「強制異性戀」與現代較常見的「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或在台灣常用的「異性戀霸權」(heterosexual hegemony)有相似之處,但三者側重的點有所不同。
「異性戀常規」一詞常出現在英文世界,它大約在1991年由美國酷兒理論家麥可·沃納(Michael Warner)所普及,指出酷兒壓迫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偏見」或「恐懼症」,而是滲透於法律、政策、家庭、醫療、教育與流行文化等社會生活中的每個層面,使異性戀成為唯一正常、自然、且不容質疑的性傾向,並使個人和社群不斷無意識地內化並再生產這種秩序。
「異性戀霸權」一詞則在台灣相對常見,其源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獄中書簡》(Prison Notebooks)中提出了「霸權」(hegemony,精確來說應譯為「領導權」)概念,係指統治階級透過意識形態、道德與知識影響,讓大眾接受其統治、正當化其經濟與文化權力。異性戀不僅仰賴經濟或政治力量,更透過教育和媒體等方式使異性戀看似理所當然,使其成為深植於日常生活的「常識」。
「強制異性戀」與前述兩者最大的不同,是它比起性傾向壓迫更強調性別壓迫。因此,異性戀並非個人身份認同,而是延續並鞏固男人控制及剝削女人的政治制度。它與女人的經濟依賴、社會地位、性別規範及遭受性暴力等問題緊密相連,不僅使女人無法自由地建立或不建立社會關係,甚至也無法完整發展自己的性認同。
強制異性戀批判的當代洞見
在當代,強制異性戀的概念仍能提供有別於「異性戀常規」或「異性戀霸權」的洞見。比如台灣和許多國家的人工生殖法律仍將單身女人及同性伴侶排除在外,正揭示出強制異性戀為了確保女人的性及生殖為男人服務,於是在壓迫酷兒族群的同時,也壓迫所有的女人。因此,「異性戀預設」並非單純只是酷兒族群受邊緣化,而是為了鞏固女人處於從屬地位的性別壓迫制度。
在婚姻平權通過的當今,強制異性戀的批判比以往更為重要。它揭示了酷兒與女性主義運動不應屈服於異性戀制度的「同化」陷阱,輕易滿足於組成核心家庭和參與主流社會,而應徹底瓦解異性戀作為父權的根基。酷兒女人不只是這場鬥爭的參與者,更位於前線,直接挑戰異性戀如何維繫對女人的控制與剝削。唯有拒絕服從、拆解異性戀規範,並與其他受壓迫群體建立堅實的聯盟,才能真正動搖父權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