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著作】認識性別流動與非二元:我可以不男不女或既男又女嗎?
Lorraine Pan
7/14/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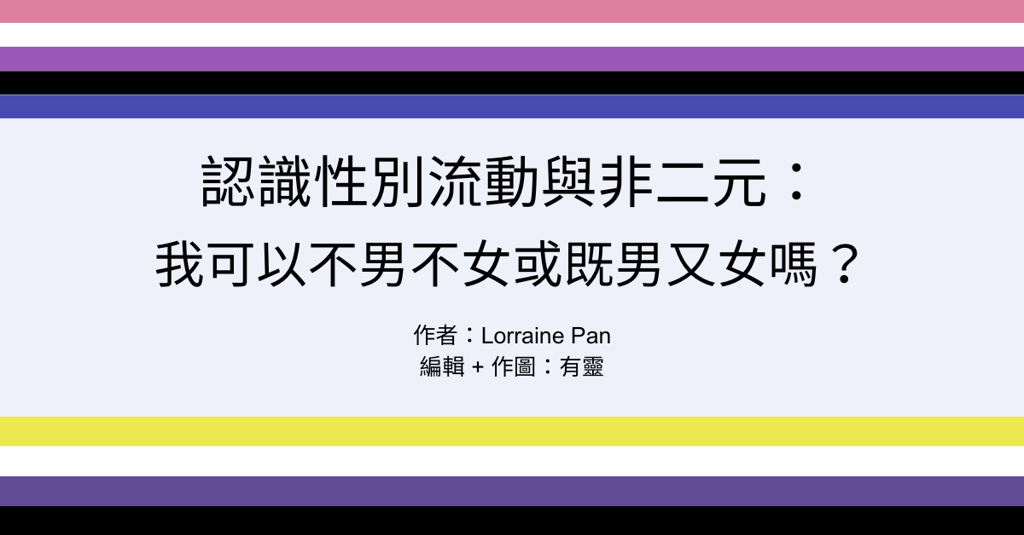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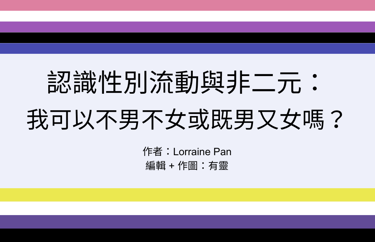
【原創著作】認識性別流動與非二元:我可以不男不女或既男又女嗎?
作者:Lorraine Pan
編輯 + 作圖:有靈
主編筆記:
酷兒翻越在今年的 #國際非二元性別日 ,邀請大家一起讀一篇來自一名非二元性別離散主體的文章,一起探索性別流動與移居移動之間的互相作用、看見非二元性別的一種交織性樣貌~
「我不敢穿裙子。」
課上教授在討論性別身分和經驗,我舉手發言時脫口而出,我不敢穿裙子。
我是一個非二元性別者,我喜歡華麗甚至被視為誇張的長裙,但我曾經因為性別不安,不敢穿裙子。我喜歡自己的身體,無論我曾經纖瘦,或是爾後更豐腴。我喜歡聽到「漂亮」的稱讚,也認為自己漂亮,出於一種與性/別無關的自信。然而,在他人眼裡,我陰柔的外貌常常與我的指定性別被連結在一起。對於外貌的稱讚之中,一些人隱藏在稱讚之下的性化凝視讓我不適,還有一些人強調我指定性別為女性時,也讓我感到不安。
我是非二元者,我希望被認可為非二元性別。為獲求來自他人的認可,我不得不做出一些捨棄,而使我看上去更「非二元」。大多時候,這種壓力來自酷兒社群之外的主流社會,有時,酷兒社群內部的同伴無意間說出的話,比如「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覺得你不太『酷兒』」也會帶給我壓力。當我頻頻穿著裙子而被指「看上去很順性別」或「看上去很女」時,我便感到,自己喜愛的裙子和頗為驕傲的身體,似乎給我帶來了一些困擾。
常有人指摘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群體,稱「你連這些努力也不想付出,就想被別人認可嗎」。這種問題其實可以反過來問,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需要付出那麼多努力才能夠被別人認可的社會嗎?即便是順性別,也飽受著性別刻板印象和社會期待的傷害——順性別女性被要求溫良恭儉讓,順性別男性被要求強壯不落淚。而這種壓迫放在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群體身上,使得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者不得不順應另一套雖然形式不同、但核心相同的規訓,但他們卻在一些時候同時被指摘「鞏固刻板印象」——這是有失公允的。無論順跨與否,任何人都有自由表達性別、而不受束縛的權利。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群體的自由和正義,是一場讓所有人都受益的革命。
如果說表示性別身分的名詞是一個標籤,那麼,我還沒想清楚用什麼標籤來形容自己。
我有過一些認可自己「女性身分」的時刻,並非因為我出生證明上寫著「女」,也不是因為我的身體和器官,而是在社會生活中一些與女性氣質相關的生命經驗。比如說,在書寫自己作為倖存者的經驗、或是與其他女性共同呼籲抵制性別暴力時。儘管我非常清楚,倖存者不只女性,女性主義也不只關注女性,但我生命和成長裡的很大一部分創傷與苦痛,與我在社會當中作為「女人」形象生活的經驗緊密相關。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應該被指定性別、外貌表達和社會賦予的性別期待所綁定,而我也深知這與我用「女性」的視角來解讀和表達自己過去的經歷並不衝突。
而有些時候,我又偏向光譜的另一側。我曾經嘗試束胸,也剪過平頭。有人用「鐵T」來形容我,有人說我像個男孩。我對於身體邊界和外貌表達的嘗試,和我的性別探索歷程緊密相關。我並不確定我在國中身體開始發育時選擇束胸,是因為我當時作為一個缺乏性/別教育的青春期女孩,曾經對於身體變化感到羞恥、尷尬,還是因為我開始對自己被期許著循規蹈矩的女性形象和角色感到質疑。或許兩者並不能分離,而困惑、不解本身,也不是一種過錯。不理解性別,也是一種對性別的理解。
在我19歲剪平頭時,也有人說我「看上去更酷兒了」。我對這個評價很滿意,它極大地緩解了我對於自身性別表達的焦慮。作為非二元性別者,我也常常感到性別不安。我喜愛蘿莉塔服飾,又曾經十分喜歡粉紅色,因此過去常常穿著一身粉紅色的洋裝,搭配粉紅色的頭飾、皮鞋出門,朋友有時會說我「看上去與順女沒有兩樣」。儘管我認為自己喜歡粉紅色的搭配和自己的性別認同毫無關係,但就像跨性別者常常擔憂自己是否夠 pass 一樣,我焦慮自己如果看上去不夠中性,就不夠資格被稱為酷兒、非二元性別。
非二元性別和性別流動,對我來說,不是一種標籤,相反,是一種去標籤化的形容。這代表著我可以用更多元、自由地方式表達自己,而不必歸屬於男或女的任何一端。想像一個全新的性別面貌,不是非男即女,而是可以不男不女,或是既男又女。我既可以和順性別女性保持一段距離,又可以不必完全進入跨性別男性的空間。我既可以透過女性的視角理解自己的生命經驗,又可以用中性和陽剛氣質的外貌與社會相處,來呈現自己的新樣貌。我的性別身分隨著我對於不同事物的感知和經驗流動,也隨著我對於自身的理解和表達的累積而產生變化。我的性別之複雜,就像我的生命歷程本就豐盈、精彩一樣。
對於跨性別和非二元社群裡的其他同伴,我常常和他們說,不必過於苛求自己符合社會期待的框架,讓自己舒服才是最重要的。但對於自己,我卻謹小慎微地思考自己該如何呈現自己的性別樣貌。人無法完全和社會抽離,而我對於他人展現出包容,也是因為我希望營造包容而友善的社會,也同時被包容地對待。很長時間以來,我都過於自省——我提醒自己相對於酷兒社群裡其他有手術和醫療需求的跨性別者,擁有更多更夠生存在社會上的優勢和特權,卻忽視了自己作為非二元性別者,也被二元性別體制壓迫著。周身的社會對於我的誤解和歧視並不比任何人少。新認識我的人,常常脫口而出使用「she」來稱呼我,我雖感到有些不適,卻很少主動糾正別人,告訴別人我的代名詞是「they」。當我的朋友主動為我向別人糾正我的代名詞時,我甚至意外地驚喜,感到受寵若驚,儘管這是我本就該得到的尊重。有時,在我表現自己對於中性氣質的追求時,一些人會用「你就是很順女啊」來觸發我的性別焦慮。還有的時候,我用女性的視角書寫自己的生命經驗,亦有人刻意嘲諷我同時使用非二元性別來描述自己是「順性別假裝進步」。
我過去以為自己身為非二元性別者所面臨的壓迫比許多人都輕,正如我曾經以為身為無浪漫者可以通過隱藏自己而避免受傷,相較於一些因為同性性傾向而受到惡意對待的同志族群擁有更多特權,因而需要常常自省一樣。這種對於自身身分的壓抑和對於所受壓迫的忽視使得我在受到誤解和歧視時,痛苦被進一步地放大了。而現在,我選擇感受自己的困惑與苦痛,表達和理解自己的身分。在自我成長的過程裡,我也認識了許多酷兒社群裡的同伴。與彼此之間的交流和分享讓我意識到,我與許多朋友都或多或少共享著一些生命經驗,這些共同的困惑與喜悅,使得我們產生了超越浪漫愛的情誼。
性別身分常常與我的其他身分緊密相連,比如我的族裔。學者們討論跨國遷徙時,常常用離散經驗來探討跨境分散的族群在不同地域和國境間的矛盾與苦楚。在我看來,跨性別、非二元性別、性別流動者和其他各式的性別酷兒,本身就有「性別離散經驗」。在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間,個人對於性別的探索與跨國遷居者對於族裔身分的探索,是相似的,既充滿苦楚,也飽含感動。
我是第一代移民。18歲以前,我在中國長大。後來,我遷居至加拿大。我也同時認識了來自台灣、香港,和世界各地各國的酷兒朋友們。在中國,我有時是中國人,有時是漢人;在加拿大,我更多時候是被用「亞裔」一詞來稱呼和指代。我生命裡的一部分紮根於東亞和中文社群,而另一部分則使用英文和北美語境來書寫。我既喜歡亞洲藝人(如 IU),又深受美國流行音樂(如 Chappell Roan)的影響。我既閱讀吳明益、張亦絢,用中文書寫散文、小說,又閱讀 Audre Lorde、Bell Hooks,用英文表達和創作。作為一名有著跨國遷徙經驗的酷兒和離散者,多重身份使得我受到的壓迫多重、交疊,並以一種幽微、隱形而複雜的方式呈現,但同時也給予我看待事物時更多元和深刻的視角。接觸到不同背景的跨國酷兒,幫助了我更好地認識和表達自己。
對一些人來說,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是幾乎完全重合的;對一些人來說,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之間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惟有跨越才能尋回自我。對我來說,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兩者,都是在不斷延伸與變化的空間——這兩個空間會碰撞、會衝突,也會交疊。
如何用離散經驗來理解性別?在遷居至加拿大後,出於過去的創傷經歷,我曾有一段時間拒絕使用中文語言,也刻意疏離與我的出生相關的文化;而在性別表達上,我也曾經一度刻意追求陽剛和中性的外貌,以建立一個不同於指定性別的性別表達。然而,在不斷認識不同身分的人,和不斷理解自己的過程裡,我逐漸意識到:語言和文化涵蓋之廣闊,並不受我所反對的政府和國家所綁架;而性別的樣貌呈現之豐富,也不受刻板印象和社會期待所限制。我於是在經歷一系列對於自身國族文化與性別認同的探索之後,重新認識自己的出身和成長,既保有在出生之地習得的一些文化,又敞開欣賞遷居之所的風景;既接納指定性別帶給我過去的生命經驗,也想像和追求一個不被指定性別綑綁的未來。
我認可出生作為生命的一部分,並非認為指定性別不可抗逆,也不是對於性別本質主義的屈從,而是在獨立於過去所受的規範之外,對自己有重新的理解與接納;我將成長過程中學習到的新事物融入對生命的理解,並非是對自己的過去有所厭棄,也不是全然被動地接收外界的訊息,而是用自己的經驗和視角理解和詮釋新鮮的事物,實踐一個屬於自己的、全新的成長。離散之間,建立一個超越單一想像和框架的空間,我學會接納自己的不同面向,連結過去與未來。
In-betweenness——多重的身分使得我的成長多了一些崎嶇,但也展現了我生命的厚度與豐富。
如今,我使用「they」作為我的代名詞,以方便他人稱呼和指代我。但對於自身處在性別光譜上的什麼位置,我仍然未有一個相當明晰的定位。幸得非二元性別和性別流動這一理念,給予了我一個更寬廣的世界,令我有一個空間讓我更全心全意地感受和探索自己的生命。未來的我會如何認識、理解和表達自己的身分呢?我會更男、或更女嗎?我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現在的我知道,沒關係,慢慢來。生命那麼複雜,要用一生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