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與代孕
翻譯著作女性主義
希維亞
3/17/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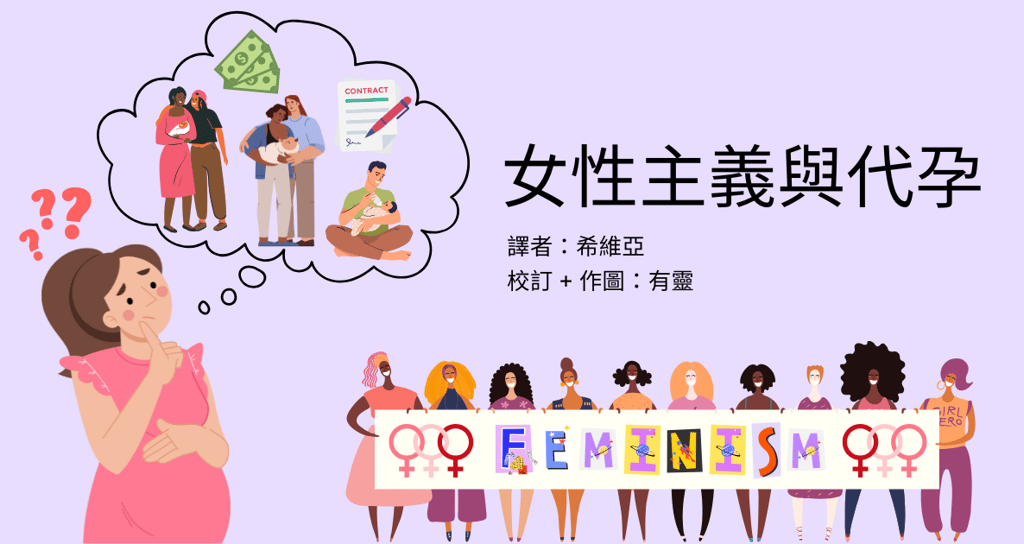

【翻譯著作】女性主義與代孕
本篇文章原刊於 Surrogacy Blog
原文作者:Sarah Jefford
譯者:希維亞
校訂者:有靈
作圖者:有靈
譯者筆記: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長年推動代孕合法化,而由國眾兩黨去年提出的代孕法案又涉及商業剝削、人口販運和危害代孕者健康等重要疑慮,引發婦女團體的強烈抗議。因此,在台灣社群媒體上的進步勢力和性別議題討論社群,幾乎一面倒反對代孕。
然而,什麼是商業代孕、什麼是非商業利他代孕、什麼是剝削或販運,這些似乎都沒有很好地展開細緻討論。在網路上,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人經常被扁平化,彷彿只有殘忍、欠缺性別平等和兒童人權意識的人,才可能會抱持此立場。
故翻譯本文,雖非完全符合譯者的代孕立場,但希望將澳洲代孕制度的現狀,以及將支持代孕的女性主義論述帶進台灣輿論場域。生育本身和相關法規並不完美,但或許仍能找出不同立場之間的共識和平衡點。
女性主義與代孕
任何女人都擁有完整的身體自主權是女性主義核心理念之一。這包括生殖自主權;決定是否要生、何時生、生幾個孩子,以及就生殖和生育層面的決定權利。我是一名代孕者,也是一名女性主義者;我致力於將多元交織視角融入我的女性主義實踐。當我成為兩個男孩的母親,後來在一個原住民族組織工作時,我的女性主義理念得以體現。我意識到自己身為白人的特權,還有身為一名女性所面臨的不利處境,並反思了我的兩個白人兒子在一生中可能會有的不同經歷。
我運用我的身體自主權——捐卵、成為代孕者——來幫助需要的人。這個決定是與我的伴侶討論過的——並非他可以告訴我該做什麼,而是因為我們是個團隊,這是個團隊的決定。我將成為捐卵者的決定和我們的孩子哺乳相比擬——我的身體,我決定。任何人都能告訴我該如何處理我的身體、或我的基因,對我來說是一種侮辱。
作為一名擁有良好生育能力和健康的特權女性,我想幫助沒有我這種特權的人「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可能影響了我決定在澳洲同性婚姻平等辯論期間幫助一對男同志伴侶做代孕的決定。當然,能在沒有太多阻礙下做出生殖決定,而不像許多男同志和遭遇不孕困擾的女人一樣,我感到非常幸運。
然而,一些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人對所有形式的代孕都抱持著高度的批判態度。我仔細思量過他們的觀點,並反思了自己作為代孕者和代孕律師的經歷。雖然我不那麼同意他們的批判,但我思考過如何幫助促進澳洲的最佳代孕實踐,並教育人們如何做出充權、道德的跨國代孕決定。
對代孕的批判可以總結如下:
1. 代孕等同於兒童販運或「販嬰」
在澳洲,代孕者不會獲得報酬,任何收入都是用來支付他們的開支。他們不是為了孩子或履行契約義務而收取報酬。澳洲的代孕安排要求代孕者保有他們的身體自主權,協議是無法強制執行的。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權利是最優先的。如果代孕安排出現問題,誰對孩子負責以及孩子住在哪裡的決定,將把孩子的權利視為最優先的考慮點。在澳洲,不可簽訂關於孩子的契約。縱使並不完美,但澳洲的代孕諮詢和法律程序,要求各方考慮透過該安排出生的任何孩子之權利和利益。
2. 代孕是剝削的,否定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一些批判者將代孕和性工作相比擬,因為他們聲稱代孕涉及女人的身體商品化、將女人的身體視為滿足他人目的之工具。批判者聲稱,代孕對女人來說是性和生殖的苦役。在一些國際代孕案例中,這種批判可能是合理的——尤其是代孕者生活在貧困中,並因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而被契約限制的情況下。有些契約內容令人反感,包括建議如果他流產就無法得到報酬的條款。對代孕者的身體和自主權的控制涵蓋限制他的行動以及要求他遵守嚴格的生活條件。平心而論,在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這些情況發生的機率較低。
在澳洲,代孕者保有他的身體自主權。雖說各方之間可能就代孕者的行為和生活方式達成協議,例如他在懷孕期間不喝酒,但這是不可強制執行的。我向在澳洲進行代孕安排的準家長強調,代孕者最終可以決定他在懷孕期間所接受的照護,並且他可以同意或拒絕接受任何治療,包括終止懷孕。
女人有權決定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包括代孕和性工作。女性主義者應為做出充權選擇的充權女人感到高興。如果我們擔心女人(作為代孕者或性工作者)被剝削,那麼我們應該管制這些行業,並支持每個人為自己做出知情和充權的選擇。貶低或使性工作或代孕成為犯罪行為並不能保障女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傾聽代孕者或性工作者的聲音,支持他們行使自己的自主權。我們不需要其他人替我們代言。
3. 沒有獲得孩子的權利;無法自然受孕或懷孕的人必須甘願於沒有孩子的現狀。
在這個議題上,我在某些層面與批判者意見一致——人們並不擁有獲得孩子的權利。我們被灌輸了一種社會觀念,認為長大後,就應該找到一個伴侶安頓下來,並生養子女。在不生養子女的條件下,有許多方式活出幸福和充實的生活。每個人都應該自由選擇是否要孩子——這代表著改變我們如何看待沒有孩子的女人,並且不施壓人們去生孩子。
雖說我不認為任何人都有權利獲得孩子,但我仍然替一對想要孩子的伴侶代孕。我堅持我有身體自主權和生殖自主權等權利,並且孩子的權利始終被視為最優先的。我所生的嬰兒得到了很好的照顧與愛護。一般來說,我們的社會已接受孩子可以由兩位父親撫養,並不會對孩子的健康造成任何損害。我和孩子的雙親的主要關注點始終是他的幸福和自我感受。他將永遠與我和我的孩子保持關係,我會支持他的利益,並在他需要時提供幫助。
4. 抹消母親的存在
這種批判認為,只有生產的女人才能擔任母親的角色。研究顯示,生產嬰兒的女人與嬰兒之間存在著原始的聯繫——作為一個為另一對伴侶生孩子的人,我可以證實這一點是真實的。我與我所生的嬰兒有了聯繫,也許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基因,他看起來像我和我的家人。然而,我也可以證實,懷上和生下他,並沒有使我想和他在一起或撫養他。我懷上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以雙父撫養,我百分之百開心和滿足地這麼做。
我聽說過有些人批判放棄一個嬰兒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母職和母親角色。我認為這說法是簡化的,過於傾賴商業化的母職形象。這也假定只有母親才能照顧孩子。我已經寫了更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挑戰了女性被認為天生就是母親,或者只有和母親在一起、孩子才能茁壯成長的想法。
一些批判者認為,出生證明上不包含生母的資訊等於將他從孩子的歷史「抹消」掉。這是我願意接受的另一個批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如此。澳洲目前的程序是,原始的出生證明上列出代孕者和他的伴侶作為家長。當「家長關係令狀」(Parentage Order)獲得批准,就會發放新的出生證明,「家長」一行列出負責撫養孩子的家長。大多數代孕者對出現在一個他不認為是自己的孩子的出生證明上,即使是短暫的,感到不舒服。但是,是否有理由出生證明不能列出除了家長以外的其他資訊呢?對於孩子來說,將其生父母、任何捐贈者和負責撫養他的家長列在出生證明上,是否更符合其最佳利益?在文獻上刪除代孕者,確實可能會抹消生育、基因和代孕者本人的真實歷史。為什麼出生證明上只列出了兩個爸爸,好像在受孕、懷孕和生產中沒有女人參與一樣?如果批判者認為這是抹消,我們能否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承認代孕者並承認準家長?約翰·帕斯科(John Pascoe,前家庭法法院首席法官)在2016年關於孩子權利的路易斯·沃勒講座(Louis Waller Lecture)中詳細闡述了這個想法,主張孩子有權利知道自己的歷史。在一些司法管轄區,其實有整合的出生證明選項。
抵銷批判者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將對代孕的批判與我們進行代孕的原因相互調和。我意識到這些批判者永遠說服不了我說,所有的代孕都是邪惡的,我也永遠說服不了他們代孕有多令人驚艷的可能性。我所意圖實現的女性主義版本致力於充權女人做出充權的決定,任何試圖否認此一權利的人在我看來都不是女性主義者。
一些代孕的批判者仰賴將一些少數女性的糟糕代孕經歷作為證據。確實,去預設所有代孕都是好的、所有結果都是正面的,非常不切實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少數故事竟然被用以支持全面廢除代孕,或強化那些聲稱我們都遭受剝削論者的觀點。我並非戴著粉紅濾鏡看待代孕;我知道大多數代孕並不完美,我們都可以做更多來讓它變得更好。
孩子的權利應始終是最優先的。此外,如果要保護代孕安排的完整性,我們必須確保代孕者的身體自主權。最終,每個女人都有權決定是否為他人懷孕,我們應該提供適當的架構來確保他的權利得到保護。廢除代孕不是答案;管理才是關鍵。
我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別在墨爾本大學法學院的健康法律與倫理研討會(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School’s Health Law and Ethics Seminar)上發表演說,您可以閱讀我的講稿:「代孕如同母性:不可剝奪的選擇權」,其中詳細闡述了這些主題。您也可以閱讀我的有關最佳代孕實踐以及我們如何確保促進代孕者和孩童的利益及權利的思考。
如果您對代孕還不太了解,您可以透過閱讀Surrogacy Blog,下載免費的代孕手冊,以及收聽Surrogacy Podcast來了解更多有關流程的資訊。
我寫了一本書,《不僅僅是個寶寶:給準家長和代孕者的代孕指南》(More Than Just a Baby: A Guide to Surrogacy for Intended Parents and Surrogates),您可以購買紙本書或電子書。
關於原文作者:
嗨!我是 Sarah Jefford(代名詞為「她」)。我是一名家庭創建律師,職業於代孕和捐贈懷孕安排領域。我是一位試管嬰兒的媽媽,也是名卵子捐贈者和傳統代孕者,在2018年為兩名父親生下了一個孩子。我倡導在澳洲建立正面的、最佳實踐的代孕安排,並提供支持和教育,幫助準家長在尋求海外代孕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