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羅琳對無性戀的攻擊:恐跨與無性戀敵對主義的關聯
翻譯著作無性戀女性主義
希維亞
4/10/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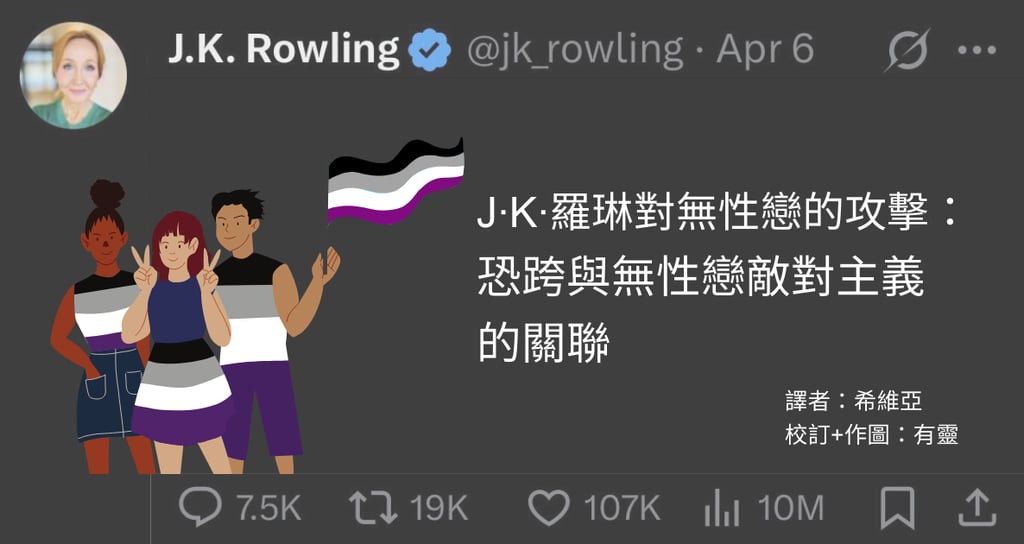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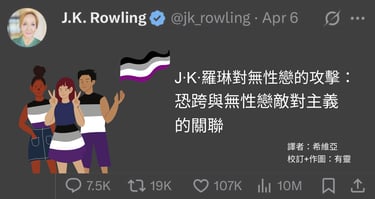
【翻譯著作】J·K·羅琳對無性戀的攻擊:恐跨與無性戀敵對主義的關聯
本篇文章原刊於 The Sociologist Speaks
原文作者:Canton Winer
原文出版日期:2025/04/09
譯者:希維亞
校訂+作圖:有靈
主編筆記:
在今年的 #國際無性戀日,J·K·羅琳在推特上嘲諷無性戀者所面臨的壓迫是「假」的,此後引起全球無性戀社群的怒氣與回應。在這件事情上,酷兒翻越選擇翻譯專攻於無性戀研究社會學家 Canton Winer 的文章,因為本文很明確地指出羅琳反對跨性別和無性戀背後的兩種邏輯:第一是性別法西斯主義中的生物決定論,第二則是「解放是有限資源」的零和遊戲思維。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無性戀與跨性別所受到的敵對待遇,局部可追溯於排跨基進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批判、精神和政治的歪解。羅琳和TERF們的壓迫奧運、解放零和遊戲邏輯,值得我們所有人反思和批評,以下譯文提供參考~
「祝所有想讓完全陌生人知道他們不想約炮的人,國際假壓迫日快樂。」
—— 羅琳在推特上這樣寫道,以此來嘲諷「國際無性戀日」。
羅琳是個眾所周知的恐跨者(transphobe),所以她對無性戀的攻擊並不令人驚訝:反跨性別與反無性戀的態度之間有著既定的連結。
有一些無性戀者多年前就意識到了這種連結,甚至有句話說:「剖開一個恐無者(acephobe),你會發現一個 TERF(指的是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但是 TERF 這個詞實際上具有誤導性,因為這些人既不基進,也不真正支持女性主義)。」
羅琳對無性戀顯然一無所知(並且顯然懶得去了解)的這個事實先不討論,我想討論另一個問題:
攻擊跨性別者和無性戀者之間有什麼連結?
我無法在這篇文章中完全回答這個問題,但讓我們先觸及一些重要的主題。
性別法西斯主義
對無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攻擊,都是由法西斯式的、威權的性別觀所驅動的。
法西斯對社會性別/生理性別的看法是:只有兩種——「男人」與「女人」。你的性別是生來就決定的、是「自然」的,而你無權選擇。
跨性別者之所以遭受法西斯的攻擊,是因為他們挑戰並動搖了這種威權世界觀。禁止跨性別醫療照護、阻止他們參與公共生活,這些手段都是為了強迫人們服從這樣的法則:你的性別是與生俱來的,你必須遵守它。
在法西斯政權下,女人的一個核心角色就是提供性(以及生育孩子)。這是女人的「自然」職責。(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分子只支持「合適」的人們生育孩子;在法西斯政權下,種族、族群或宗教上的少數群體往往面臨相反的壓力,例如強制絕育。)而男人的「自然」職責之一則是傳宗接代。因此,對無性戀者的攻擊就出現了。
羅琳也許會否認這種解釋,但她與其他恐跨者所汲取的思想源流顯而易見。也許,如果她少花點時間在推特上,多去圖書館,她就會意識到這一點。
反對「字母湯」
許多最響亮的反跨聲浪,對「LGBTQIA+ 字母湯」(LGBTQIA+ alphabet soup)也充滿敵意。
為什麼?因為如果唯一「自然」的性別認同是「男人」和「女人」,那麼「異性戀、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之外的所有性傾向都是「不可能的」。
羅琳近來對無性戀的敵意,更加暴露了她的真面目。她對酷兒族群的問題顯然不限於跨性別者。很可能,她也反對其他「假」的酷兒認同,因為這些身份認同挑戰了所謂自然的性別二元,例如泛性戀、非二元性別、性別酷兒、性別流動、無性別以及間性人等身份認同。根據我經常收到的來自TERF粉絲的留言,我敢打賭,她認為「酷兒」這個詞也是「捏造」的。
羅琳或許特別執著於對跨性別者的敵意,但她對無性戀的攻擊表明,她對 LGBTQIA+ 這個「字母湯」中的許多其他群體也毫無善意。
「你才沒被壓迫!我才有!」
另一種推進反跨與反無性戀態度的動能,是將壓迫視為零和遊戲。
換句話說,像羅琳這樣的煽動者,將壓迫視為一場競賽。
羅琳與其他恐跨者經常聲稱,跨性別者(特別是跨性別女人)「傷害」了女性權益。
我們來拆解一下這種說法。由於禁止跨性別者參加女子體育賽事是一個熱門議題(縱然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超過50萬名大學運動員中,跨性別運動員少於10人,占比不到 0.00002%),人們可能會誤以為這就是恐跨者關心的焦點。並不是。
再看看羅琳對無性戀者的推文:「祝國際假壓迫日快樂」。但「國際無性戀日」本來並不是關於壓迫,而是關於無性戀本身。是羅琳把壓迫帶入了這場討論。
羅琳對跨性別者與無性戀者的攻擊,來自一種將「解放」視為有限資源的觀點。否認某個群體受到壓迫,是剝奪他們獲得解放的一種方式。
換句話說,羅琳(以及像她這樣的 TERF)認為,承認其他群體所受到的壓迫,會威脅到她所屬群體(白人順性別女性)的進步。這種解放觀敵視結盟的可能性、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以及承認差異的必要性。
但這種想法不僅狹隘險惡,甚至荒謬。
羅琳與她的支持者如此專注於扮演「誰有資格說自己受壓迫」的把關角色,以至於他們對自身壓迫的真正來源徹底失焦。
跨性別者與無性戀者並不是女人受壓迫的根源。性主義(sexism)才是。
而性主義的一個基石,正是告訴人們他們有「自然」的、不可改變的身份,無法選擇,並且必須服從……這正是恐跨與恐無的邏輯基礎。
執著於受害性
羅琳思維方式中隱含的另一個假設,是她在邊緣群體的身份認同與受害性(victimhood)之間劃上等號。
如果你看看羅琳的公開言論,她極少談起慶賀女人的事。當她談論女人時,通常是將女人描繪為受害者。在這種敘事框架下,女人連帶(womanhood)等於持續不斷的受害。
這是一種對邊緣性(marginality)極為狹隘的理解。
處於社會邊緣的確往往伴隨著受壓迫經驗。但這並非全部。邊緣性同時也可以帶來社群、快樂、自我理解、行動能力,以及一種特殊光彩的存在。羅琳似乎無法正視這點,這實在讓人深感悲哀。
但請記住:羅琳和其他 TERF 往往將解放視為一種有限資源,認為你必須與他人競爭才能獲得。在這樣的框架下,獨占受害者性變得至關重要——否則,其他人可能會「占走」你的一部分解放!
然而,必須明確指出,羅琳關於「無性戀者並未受到壓迫」的說法是錯誤的。我之前已解釋過,當你生活在一個不斷告訴你「沒有經歷過性吸引力是種病態」或「錯誤」的社會中,那本身就是種壓迫。
許多無性戀者遭受來自醫療專業人士的病理化對待。事實上,一些研究顯示,無性戀者比其他 LGBTQIA+ 群體更容易被「扭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而這通常來自心理治療師和其他醫療照護者。
在某些地區的法律,如果婚姻未經「圓房」則可能被視為無效。即使這些法律壓力不存在,文化上仍然普遍認為性是「真正」浪漫關係的必要組成部分。
上述只是幾個例子,但核心問題是:聲稱無性戀者未受到壓迫,根本就是錯誤的。
最後,還是祝大家國際無性戀日快樂!
這篇文章並沒有詳儘解釋反跨與反無之間的所有關聯,但我希望這些想法利於將看似不同形式的偏見連接起來。最後,我想以較正面的筆調做結尾。
羅琳顯然對無性戀的能見度感到煩躁。諷刺的是,羅琳對無性戀概念的厭惡,反而使得「國際無性戀日」變得比以往更被看見了!


關於原文作者:
Canton Winer 是北伊利諾大學(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社會學及婦女、性別與性別研究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著重於性別和性意識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無性戀光譜上的經驗和觀點。您可以在 Bluesky 上跟進他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