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子宮:專訪紀錄片導演 欣·盧博
跨性別非二元翻譯著作
有靈
3/31/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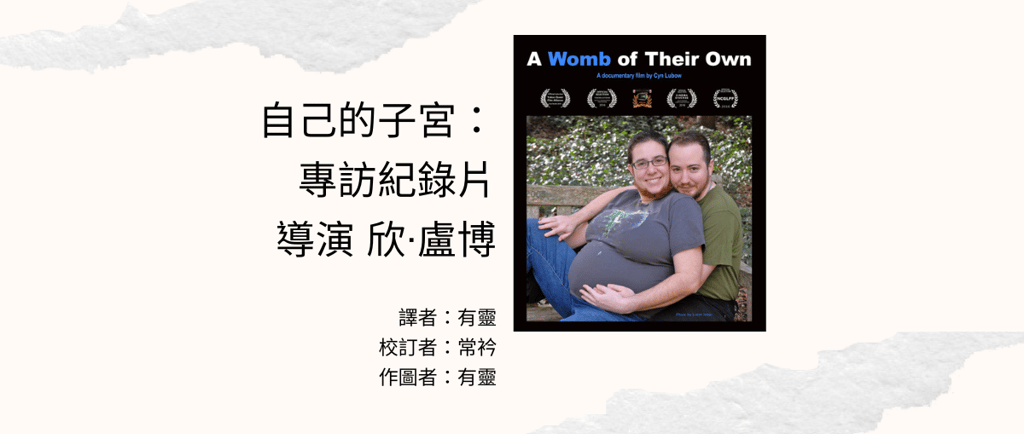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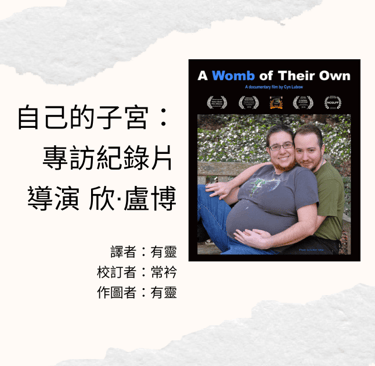
【翻譯著作】自己的子宮:專訪紀錄片導演 欣·盧博
本篇文章原刊於 Mutha Magazine
原文作者:查理·金·米勒(Charlie King-Miller)
原文出版日期:2016/10/26
譯者:有靈
校訂者:常衿
作圖者:有靈
譯者筆記:
在今日的 #跨性別現身日(#TransDayOfVisibility),酷兒翻越要為一個特定族群發生:多元性別社群中的分㝃者。《自己的子宮》(A Womb Of Their Own)是一部展現出六位跨性別男性、非二元/性別酷兒及認同中性/陽剛(masculine-of-centre-identified)人士之懷孕、分㝃及胸餵(chestfeeding,意指「哺乳」或「餵奶」的性別中性術語)經驗的紀錄片。近期台灣談起《人工生殖法》修法案時,大多數的公共討論忽略了跨性別生育力的存在與需求,尤其是具子宮的跨性別、非二元及多元性別者。我希望這篇導演專訪可以讓更多人看見跨性別和多元性別社群中的生育力,並且將「孕婦」、「分娩」、「餵奶」等女字旁的詞彙去性別化。酷兒翻越目前正在跟導演談判放映權,預計夏天在台北舉辦至少一場放映。
身為一名性別酷兒的T,懷孕讓我感到非常孤單。 醫生會對我性別錯稱,原本的衣服穿起來也不對勁,這個世界似乎一下子突然無法解讀我的性別特徵。採買嬰兒服飾時,我有時被當成身材臃腫的T,引來許多異樣的眼光;有些陌生人看出我懷孕時都稱呼我「媽媽」,儘管我的外表看起來不太像。雖然我理性上知道有許多生育小孩的跨男和非二元者,但我身邊完全沒有類似這樣的人存在。
女兒出生三個月後,我的助產師建議我去看一部新的紀錄片。儘管帶著寶寶去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聽起來很恐怖,我知道自己非去不可。欣·盧博(Cyn Lubow)執導的紀錄片《自己的子宮》(A Womb of Their Own),探討的是不同跨陽剛認同者的懷孕經驗。這就是我孕期間所需要的那部片。我在片中那些侃侃而談、心思細膩的被攝者身上,看見自己的身影。儘管他們的經歷與我不盡相同,但這些故事的多樣性和深度為像我這樣的人撐起一片天。這部片是對那些經常強迫施加在待產者身上的女性期待的正面回應,也是我們此刻所迫切需要的良藥。
我最近剛與盧博共渡一段美妙的訪談時光。能夠在看完片幾個月後相聚,聽聽這部片所收到的熱烈迴響,真的是太棒了。
–– 查理·金·米勒(Charlie King-Miller)
查理·金·米勒(以下簡稱金):當初為什麼會想拍這部片?
欣·盧博(以下簡稱盧):拍這部片的初衷,是想要跟自己混雜的性別認同獲得和解,並進一步了解跳脫女跨男和性別二元的性別可能——為無限變化的性別體驗和表現爭取空間。我想質疑人們對性別的任何假設,並呈現那些發現自己被排除在文化認可的性別期望之外的人的經驗。
金:當初你是怎麼找到片中的拍攝對象?
盧:我用了許多不同的方式,也碰壁了許多次。我用關鍵詞在網路上大量搜尋,找到一本名為《孕T》(Pregnant Butch)的圖像小說/回憶錄,並由此連絡上這本書的作者 A·K·桑摩思(A.K. Summers)。我在性別奧德賽(Gender Odyssey)研討會期間的育兒工作坊遇到洛倫佐·拉米雷斯(Lorenzo Ramirez),他在工作坊上分享自己身為單身跨性別父親的經驗。研討會期間我也跟每位遇到的人提我的拍片計畫,有位與會者告訴我,他前一晚跟朋友聚餐時,正好聽友人提起他女兒就讀的高中,有位留鬍子的老師似乎懷孕了,我就這樣循線找到 芮·古德曼·拉克(Rae Goodman-Lucker)。達茜(Darcy)是我一位跨性別導演同事的朋友,摩根(Morgan)則似乎是透過芮介紹才認識的。我在網路上找到了亞琳·伊什塔·列夫(Arlene Ishtar Lev),她是一位諮商師/教授/作家,專門研究酷兒、跨性別者及其家庭,她介紹了一位住在紐約奧爾巴尼的被攝者給我,但我後來沒有用他的訪談。至於芮·達羅(Rae Darrow),我記得他是自己透過社群媒體聯繫上我,而我最終只使用了那次訪談的靜照。
金:我很喜歡這部影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能在片中看見自己。跨性別或性別不羈的懷孕經驗,經常被簡單化約成一種敘事,那就是托馬斯·貝蒂(Thomas Beatie)的故事,而這個敘事忽略了像我這樣的人。我想請問,你是否一開始便把多元性當作拍片計畫的重要環節,還是說,這比較是由於被攝者的多元背景而衍生的副產品?片中的被攝者如何形塑了整部片的調性?
盧:多元性確實是我找尋拍攝對象時的主要考量之一。我想透過這部片傳遞一個觀念:凡是用來界定性別的規則,都必然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破除所有的性別規則,讓每個人都能自在做自己。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挑戰指定性別不可動搖的觀念,而我希望大家能進一步意識到,一個人可以既非女也非男,既是女也是男,性別可以流動,男性也能懷孕,女性也能留鬍子,性別元素可以任意混搭,而且不論任何性別的人,都能自在地享受自己的性別。只是找一兩位背景相似的被攝者來拍,恐怕無法有效傳遞這個觀念。 我希望盡可能讓更多人在我的被攝者身上看到自己,因為像我們這樣不符合二元性別框架的人,很少在媒體中看到自己,而就像那些白人順性別異性戀者一直以來所享受的,我們需要的是在影視作品中看到更多與我們相似的身影。兼顧族裔多樣性非常挑戰,我花了兩年才勉強滿意。至於地域的多樣性,雖然我已經盡力找尋,但還是做得不夠好。就年齡層、育兒階段、社經文化背景、性別認同、性別表現、性傾向和其他因素而言,我想這部片有呈現出一定的多樣性。
至於被攝者如何形塑本片的調性,除了他們的口才和魅力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性別的自在,以及他們所散發出的滿滿正能量。探討多元性別的影像作品,往往聚焦在被攝者的痛苦和掙扎上。在這種再現背景裡,我所採訪的人做出了基進行為,他們表現出了喜悅和自在的一面。
金:我在丹佛看的那場放映,現場觀眾幾乎都是順性別異性戀。你在映後座談時花了不少心力給他們科普多元性別的基本知識和用詞。宣傳影片期間,你是否必須做很多這樣的解釋?這如何改變你對這個主題的看法?
盧:拍這部片時,我設想了兩種觀眾:一種是跟主角們的認同狀況不同、但有興趣了解性別多樣性的人;另一種則是本片最主要的觀眾,也就是那些跟主角們的認同狀況相同、會因為在片中認出自己而得到慰藉的人。我不想拍一部跨性別入門片,所以選擇不在片中解釋專有名詞——好的「跨性別101」入門片已經夠多了。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拍得讓那些不懂專詞的觀眾,也能抓到我要傳達的觀念,拓展他們的性別預設,更懂得包容不同性別的人。有鑑於此,我本來就預期在映後時回答片中沒有解釋的名詞和概念。這類問題出現的頻率其實比我想像中少。我想丹佛那場可能是最多的。
我很樂於回答觀眾的任何問題,因為我希望透過教育大眾打造更性別多元的空間,而要打造這樣的空間,我們必須破除酷兒社群自身內化的限制和無知,破除順性別異性戀者施加在LGBT社群身上的限制,還有LGBT社群內施加在不符合LGB或T主流定義的酷兒人士身上的限制。舉個例子,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女人,也絕對是個失敗的男人,因為我不符合一般人對男人或女人的期待(不能也不願像個女人,如女人般的走路和舉止,符合對於女人的文化期待;但身上的男性特徵,也不足夠讓人認定我是男人)。有鑑於跨性別如今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現實的一部分,我也可能被視為一個失敗的跨性別者,因為我不夠男人、不服用睪固酮等等。因此我試圖拓展的不只是順性別/異性戀世界的預設和期待,也包含LGBT社群以及我們自身內化的預設與期待。只要我們仍然擁抱整齊劃一的性別分類,就一定會有許多人無法被分進任何類別,而這並不是了解自身的好方法。
對我來說,拍這部紀錄片某種程度也改變了我經驗自身性別的方式。比方說,我不再使用「辛西婭」(Cynthia),因為我再也受不了這個名字了;我不再修睫毛,也不再穿胸罩。小時候我穿的是男版童裝,也喜歡戴假鬍子、穿西裝打領帶。但等到我長大出社會後,就開始覺得自己必須以女性的身分生活。現在我意識到,能夠做一個不斷變化的、陰柔與陽剛並存的自己,其實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我不需要屈就於男性、女性甚至跨性別的分類——永遠不用,只要我覺得它們不適合我。
金:你在片中有談到你自己扶養小孩的經驗。跟你當年帶小孩的年代相比,你認為現在的育兒環境對於跨性別/性別不羈的家長來說,有什麼樣的改變?
盧:我認為對於跨性別/性別不羈的家長來說,現在的育兒環境和我當年帶小孩的環境非常不同,這是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對性別多樣性有了更多的認識。我記得我和伴侶曾經參加一個針對考慮成家的女同志的互助團體,討論時談到小孩沒爸爸的問題。我說我覺得自己可以滿足小孩這方面的需求,也很樂意這麼做。另一位成員說:「我可以當最優秀的T,但我還是覺得孩子需要一個真正的男人當榜樣」。我猜想這種對話仍然持續發生(這些圈子你混得比較深,你說呢?),但我希望至少有一小部分的人知道,沒有二元的家庭結構,女性、性別酷兒和跨性別的人還是可以養出健康快樂的好孩子,一點問題也沒有。當然,這種觀念很新,傳播得也很快,所以我們很難評估現況和未來的發展。當年我選擇不用任何性別化的稱謂養小孩、不根據他們的生殖器官做任何預設時,我認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基進的事,也感到非常孤立無援。我希望這種育兒方式不那麼基進了。對我來說,這是我做出的許多基進的教養選擇之一;除此之外,我也在他們的醫療照護、教育,以及他們與科技產品和食物的關係上做出許多決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很習慣在許多領域中當個法外之徒。
金:身為一個想懷孕的跨性別或性別不羈者,常會聽到有人說,即使你是男性或陽剛認同,分娩還是會讓你覺得很女性化。影片中的主角們如何反駁這種說法?你自己可曾遇過類似的情況?
盧:懷孕和胸餵(chestfeeding)對性別認同所產生的變化是我訪問被攝者時的主要關注。有人說他「至少有一段時間確實感覺自己更女性化」,也有人說他「沒有感到性別上有任何變化,自始至終都覺得自己很陽剛」,各種說法都有。我懷孕的時候,對於性別還沒有想得像現在這麼多,但此刻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就將懷孕當成另一件很有挑戰、但並非應付不來的計畫,跟籌備研討會,以諮商心理師的身分承接並修復別人的創傷和憂鬱,準備證照考,寫書,蓋房子等沒什麼不同。懷孕和胸餵的經驗確實非常獨特——不同於我經歷過的任何其他事情,確實不可思議的美好,也不是順性別男性能做到的事。我是作為自己經歷那次懷孕的整個過程,並不是以另一個更女性化的身分。但話說回來,二十四年前的我跟現在相比,當時的男性認同顯然沒那麼強烈。我的性別很繁複、混雜,而且始終在改變。就像代名詞和廁所一樣,我想如果我們不再將一切的事物區分為男性或女性,陽剛或陰柔,不由自主地將一切冠上名號、貼上標籤,許多人都能因此鬆一口氣——我實在不懂這麼做有什麼必要。
金:你希望觀眾看完這部片能帶走什麼?
盧:我對這部片的主要期待,是能徹底打破所有觀眾對自己或他人的性別假設和規範,並且鬆開性別結構,讓所有人的性別經驗包容在其中。我也希望片中經常可見的幽默橋段,能令觀眾開懷大笑,並感受到盡情探索自身性別所帶來的正能量、自在和玩興。最後,我也希望觀眾能從此不再疏遠非二元性別者,這其中也包括他們自己。
金:你曾經擔心過觀眾會如何評論這部片嗎?這部片的迴響如何?
盧:觀眾的反應還滿兩極的。套用我自己的說法,這部片得罪了所有人,不只是那些性別二元框架很僵固的順性別異性戀者,連LGBT社群也包含在內。但與此同時,我也收到許多影展、酷兒夥伴和產科專業人士的來信,極力想將這部片介紹給他們的社群,世界各地的都有。我在臉書上發布預告片後,有將近25,000人點擊觀看,而且觀眾來自 125 個不同國家。放映結束後,經常有觀眾跑來找我,有些人甚至熱淚盈眶,向我表示他們很感謝我拍了這部紀錄片,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第一次真正體認到,他們同樣可以好好做自己。這部片很獨特、很基進,或許也有點超前時代,所以才會這麼有爭議性。
金:你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盧:我暫時還會繼續帶著電影世界巡迴,不錯過任何一次邀請,而這需要我現階段的全心投入。作為一位拍攝敏感議題的紀錄片導演和諮商心理師,出席映後座談讓我有機會面對觀眾,幫助他們更理解相關的知識和內容,我認為這很重要,也很有力量。 等忙完巡迴後,我想利用空出來的時間,寫一篇我已經醞釀很久的故事,關於一位諮商心理師的私人世界,在這份不同尋常、孤單一人的工作中,他必須不斷聆聽令人招架不住的秘密,幫助別人與自身的秘密共處,而這一切都不能向他人傾訴。
